前沿拓展:外国囚徒衣服品牌排行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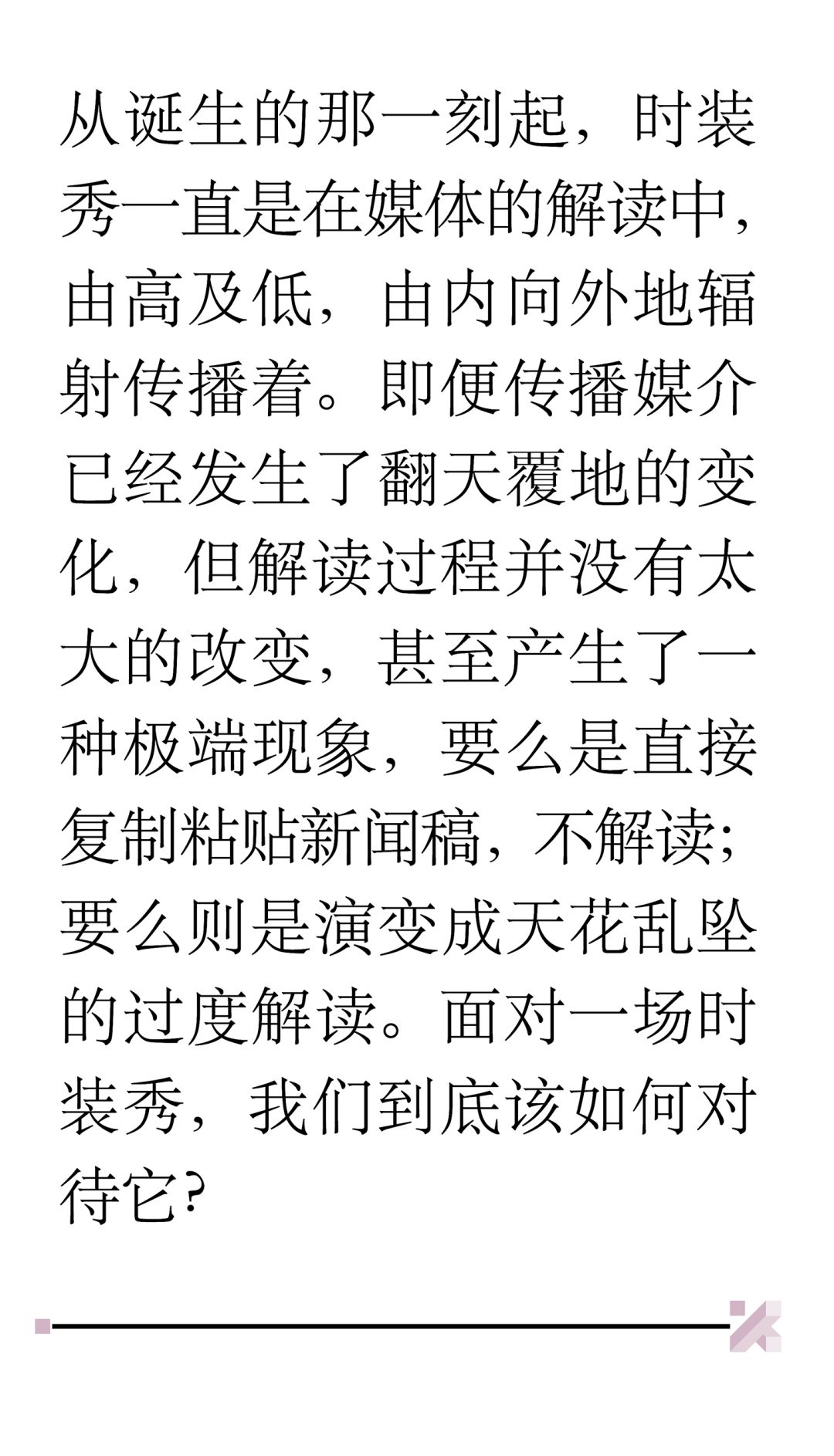
《风度men's uno》邀请到两位行业内的时尚文字工作者与本刊编辑一起,围绕该话题,举办了一场线上圆桌讨论会。

唐卓伟
《周末画报Modern Weekly》副主编

Sophie Shaw
时装作者、微信公众号“海德萧读书笔记”
 戚茂盛
戚茂盛《风度men’s uno》时装专题总监
戚:感觉一到时装周“季节”,时尚媒体,无论是传统杂志,还是微信公众号,秀评报道似乎有点陷入到被过度解读的怪圈里了。唐:过度解读的现象肯定是存在的,但我认为无论过不过头,这都是好事。这就和影评一样,很多影迷的分析后甚至让导演大吃一惊,“我压根儿就没这么想啊。”或者当我们采访设计师时,常常会问对方如此剪裁,使用这种材质是否有这样那样的意图,设计师有时会吓一跳,“我没有这么想呀,但还是谢谢你的解读。”我认为这样的解读其实是帮助读者和时装设计师建立联系,开拓了一个“异度空间”。这个空间本来是不存在的,但却通过这些“过度解读”给开辟出来了。 当我们处在一个舆论相对单一的环境中时,大家会渐渐丧失想象的能力和习惯,想象力和语言表达都变得贫乏。影评人和秀评人的“过度解读”,无论是否个人化,是否跑偏了,都是在启发和鼓励大众去想象和思考。我记得Marc Jacobs说他的作品或是时装秀完成了,他的任务也就结束了,剩下的部分交给观众,而观众的想法不是他所能控制的。第一种想法很简单,就是好或丑。第二种则可能认为“这是单调的,或者是乌托邦的,表达了乐观主义、或是抨击政治、颂扬平权”等等,这些是交给秀评人和普通观众来完成的。写秀评这事儿,我也是半路出家的,面料、打版这些我都不了解,写秀评时只能听听秀场音乐,看看秀场搭建是否有趣。Sophie: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以及阐述这个想法的背景。而时装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每个人都能从自己的背景出发,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唐:一场好的秀其实考验秀评人的知识结构。秀里引用了哪些内容,有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我可能得先看看别人怎么写的才能了解。我近发现了一个挺好用的APP,叫Shazam,一打开就能辨识秀场音乐。当然如果是重新编排过的就识别不出了。如果是原版的,APP能告诉你这是谁的哪首曲子,哪年的哪个版本。因为我们接触的公关大多不是身处一线的,他们自己都拿不到内部的资料。而这其实包裹着另一个问题,市场在中国,权力在欧洲。Sophie:中国刚加入对话,所以要慢慢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先投入的是真金白银,然后再返过去(笑)。唐:有钱没太大用处,因为他们是广告主。像LVMH集团和开云集团这些每年要砸很多钱在广告上的广告主,他们已经在限制你说实话了,大家也都知道。(笑)戚:所以除了中国在大环境下的功能本就是买货做生意以外,另一点则是我们始终不在行业的核心圈层里?如果我们去看老一辈时装评论员的文章,是不是又有别的因素?我记得有个编辑说他觉得老一代的比如Tim Blanks写的秀评越来越无趣,无观点了,也是快速改了改新闻稿之后就把稿子交了。
唐: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局限性,是出稿必须要很快。无论是老一辈的秀评人,还是报业里的时装记者,他们在没有旁征博引,在没有获得第三方资料的情况下都要快速出稿。这本身就是一种限制,所以像是Sarah Mower,她肯定是有观点的,只是没有严谨公允。Sophie:Tim Blanks的观点有时候说得比较隐晦,因为他自身的角色很矛盾,夹在品牌和媒体之间,不可能说太过分的话,所以当他不够直白时,一些年轻读者可能就一带而过了,不会去关注他话里的背后内容或是隐藏含义。我觉得小唐刚才说的影评其实也是一种“误读”,但所有对艺术的误读就是艺术的一部分,包括艺术品也是一样的。在时装里,有时候也不能说是误读,因为时装设计师本身是视觉工作者,他在设计时找了一些参考资料,创作时把这些东西融入到服装中,但他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他并非从历史角度去研究这些参考资料。这时候就给了作者想象和延展的机会。就像小唐说的,一场秀考验的是撰稿人的知识架构。不同知识架构的人看到的东西可能就和视觉工作者不一样,可能会更往前,或者领域更大,这时候的解读只要是基于设计师的灵感而延伸出来的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一场秀包含两个部分,衣服和秀。这两者的关系本身就很微妙。这几年时装体系经历了很多变化,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1990年代的时装秀,衣服本身就包含了很多信息,人们还会讨论这些衣服是否是艺术品。所以当你把这些衣服换一个语境,比如拿到一个时装展览中,它所包含的信息依然成立。但现在,时尚大环境和消费者都变了,可能是因为大型时尚集团极力地追求增长速度,秀里的衣服也变得更日常化了。
 Chanel 2019春夏系列发布会现场
Chanel 2019春夏系列发布会现场 Mugler 1995秋冬高级定制戚:当秀上的衣服变得更实穿,如果想让秀变得有趣,就要借助一些外部力量。因此秀场置景越来越宏大,典型的例子是上千人在巴黎大皇宫看Chanel的秀。我记得Kenzo的上一任创意总监把告别系列发布会办成了能容纳3000人的小型演唱会。借助这些所谓的“外部力量”,让这个商业系列更有概念或是赋予了所谓的艺术价值。请40个舞者来演绎服装,在视觉上肯定会让衣服更具艺术性。这些衣服从舞者身上脱下,穿到模特身上,又变得好卖。当然,这是一种好听的说法。如果按照以往的观点来理解,这些衣服没有任何所谓的“戏剧性”,就像你说的以前的衣服是自带戏剧性,即便是白色T台和纯白背景,就像Thierry Mugler、Jean Paul Gaultier这样的设计师当年做出来的东西是能让你“哇喔”,但现在很难了。有一次我在某个品牌的秀上睡着了,差一点从椅子上摔下去。没办法那场秀太无聊了,以至于你连报道的欲望都没有,就更别提过度解读了。Sophie:你会发现现在不管是创意总监,还是执行官,他们更喜欢用“产品(Product)”这个词。他们很骄傲于自己的产品,比如Kim Jones将手工艺结合进产品,但就算衣服设计得再好也只是好卖的产品而已,是一盘货,而不是原来的那种可以探讨艺术性的设计了。这其实是一种认知趋势的变化,很悖论,如果不提艺术性,品牌要如何让消费者接受日常的衣服有如此高的溢价呢?肯定就需要概念的加入。戚:小唐说即使是过度解读也是好的,但是我感觉现在包括咱们在内的撰稿人好像陷入到一种想要打造高考满分命题作文式的“攀比”中。比如这次时装周,我留意了几个时尚类微信公众号的稿子,感觉就是一场语文高考,作文题目是《我和我的故乡》,然后五十名考生就开始“拼”了。但这个“拼”渐渐有点变味,成了一种文字卖弄。 Sophie:说白了还是因为信息量不足。唐:本身东西的信息量就很少,是基本款。Sophie:戚戚说的“攀比”不仅仅是秀评,更是媒体本身的问题。各个品牌投了那么多钱在媒体上,他们肯定要想怎么样才能让公众号有更多人转发。媒体们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又不能采访,也没有第一手的“内幕”,如果不做过度解读还有什么办法吸引读者呢?想要更广的受众,这就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内卷”。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又没有素材的情况下,只能越来越拼。唐:我特别喜欢用俄罗斯套娃的结构去解读现在的秀,里面一层是产品本身,秀是上一层,大众的解读是外面那层。你可以说新闻稿是正史,但民间叙事也是很有帮助的,就像有一本《三国志》,还有一本《三国演义》。我们传统媒体就是“《三国演义》”,也是很认真地写的,的可读性。但民间解读可能就是“这些东西代表着品,是有钱人的东西,甚至是贪官才用的东西、来路不正的东西”。你不觉得很多在中国民间的叙事里已经变成坏品味的象征了吗?Sophie:Versace,东北人喜欢了。好吧,这是我的“刻板印象”了。唐:我觉得我们的审美是有问题的。大量的舆论宣传在文化断层之后,美其实也没了。我爸妈那时候没什么机会上学,他们给我的言传身教也是有限的。后来可以上网了,可以用VPN了,但大家发现趣味的意愿已经没有了。现在大家都在追星,整容过度成为了普遍现象。这种情况下,时尚也遭遇着一种尴尬处境,面临着过度解读或者误读,可能沦为坏品味的一部分,但同时也与这些“不正之风”联系在一起。比如你为什么不选择川久保玲?不穿Margiela呢?为什么永远都选那几个每个人都选的品牌呢?这样的选择就代表着这种选择有很大的问题。这种集体的选择就造成了民间叙述是负面的。因为美学也是需要进化的。可能小时候的你就是喜欢中规中矩。慢慢地,你可能觉得牛仔裤上剪几个破洞挺美的,再后来可能就开始欣赏解构设计了。时尚理念不断地在往前走,你也要跟上。比如我要穿了川久保玲的设计,我爸肯定会觉得我疯了。因为我爸的理念可能是保守的,而我则是先锋的。如果你不训练自己的眼睛,没有增加自己的经验,不多看不一样的东西怎么去欣赏不同的风景呢?否则的话你可能就永远选择LV、Dior和Gucci了,没关系你买呗。但对于品牌来说,产品在中国就可能会堕入一种糟糕的审美,一种负面的叙述中。可能是某个煤老板买了一条带者巨大“H" Logo的腰带。郭德纲也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但很他不懂时装。时装是一种语言,装饰主义、解构主义、洛可可,它有自己的词汇。如果你不理解这种词汇,只是凭借Logo去选择,不懂得如何用身体和时装的词汇去对话的话,后穿出来很可能是一场灾难,会把设计师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拽入一种糟糕的叙事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种奇异现象。Sophie:所以你认为杂志自己的公众号和纯粹的新媒体账号是在帮助品牌教育消费者?唐:肯定不能说都做得很好,有些就是自己拍拍照,美美地Po完图,完事儿,拜拜。Sophie:有些是用来教育的,有些是用来触及更多人群的。不同媒体的投放层级不一样,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唐:虽然很多KOL是为了挣钱,但他们的演绎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们的审美肯定好过普通人,他们用自己的品位去穿,是在帮助品牌完成一种新的叙事。但是说到教育就很难了。我承认肯定是能教育到一部分人的,比如我可能是吴岭的粉丝,我看她穿得好看,我也学她这么穿,我可能会穿得比她还好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竞争。(笑) 戚:小唐刚才说的套娃结构,如果我们还是用时装秀报道来说,这些年,媒体层面的解读和消费者层面的解读是不是很的断层了?唐:我修正一下,解读可能分三种,一种是体制媒体的解读,一种是自媒体的解读,另一种才是普通民众的解读。这三个里面,我个人觉得自媒体的解读更有趣,当然他们肯定会收品牌的钱,但他们作为个体、作为自媒体比体制媒体、机构媒体的舞姿更轻盈一些,他们的自由度更大,表现力也比我们相对要更真切。比如我挺喜欢吴岭的,她的表现就真实,所以你说的教育在某些程度上也是存在的。戚:当我们用媒体视角描述这件东西的时候,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阐述也好,介绍也好,教育也好,当一件东西成为一件商品进入商店的时候,大多数消费者还是且只是在乎它是什么牌子,以及它是否好看。而消费者对好看的理解其实还是浅显的,比如这个印花好看,这个颜色很正,这是否可以理解成普通消费者似乎就不在意品牌在讲什么故事?Sophie:我认为他们还是在乎的。那天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有趣的帖子,一个人说你怎么还买X牌这么low的牌子,我都买Y牌。底下一堆人评论,好奇怪啊,难道X牌不是比Y牌“高级”很多吗?消费者可能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是长期受媒体和自媒体的影响,消费者心中还是有一个评价体系在的,只是比较模糊,是一种感觉。
Mugler 1995秋冬高级定制戚:当秀上的衣服变得更实穿,如果想让秀变得有趣,就要借助一些外部力量。因此秀场置景越来越宏大,典型的例子是上千人在巴黎大皇宫看Chanel的秀。我记得Kenzo的上一任创意总监把告别系列发布会办成了能容纳3000人的小型演唱会。借助这些所谓的“外部力量”,让这个商业系列更有概念或是赋予了所谓的艺术价值。请40个舞者来演绎服装,在视觉上肯定会让衣服更具艺术性。这些衣服从舞者身上脱下,穿到模特身上,又变得好卖。当然,这是一种好听的说法。如果按照以往的观点来理解,这些衣服没有任何所谓的“戏剧性”,就像你说的以前的衣服是自带戏剧性,即便是白色T台和纯白背景,就像Thierry Mugler、Jean Paul Gaultier这样的设计师当年做出来的东西是能让你“哇喔”,但现在很难了。有一次我在某个品牌的秀上睡着了,差一点从椅子上摔下去。没办法那场秀太无聊了,以至于你连报道的欲望都没有,就更别提过度解读了。Sophie:你会发现现在不管是创意总监,还是执行官,他们更喜欢用“产品(Product)”这个词。他们很骄傲于自己的产品,比如Kim Jones将手工艺结合进产品,但就算衣服设计得再好也只是好卖的产品而已,是一盘货,而不是原来的那种可以探讨艺术性的设计了。这其实是一种认知趋势的变化,很悖论,如果不提艺术性,品牌要如何让消费者接受日常的衣服有如此高的溢价呢?肯定就需要概念的加入。戚:小唐说即使是过度解读也是好的,但是我感觉现在包括咱们在内的撰稿人好像陷入到一种想要打造高考满分命题作文式的“攀比”中。比如这次时装周,我留意了几个时尚类微信公众号的稿子,感觉就是一场语文高考,作文题目是《我和我的故乡》,然后五十名考生就开始“拼”了。但这个“拼”渐渐有点变味,成了一种文字卖弄。 Sophie:说白了还是因为信息量不足。唐:本身东西的信息量就很少,是基本款。Sophie:戚戚说的“攀比”不仅仅是秀评,更是媒体本身的问题。各个品牌投了那么多钱在媒体上,他们肯定要想怎么样才能让公众号有更多人转发。媒体们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又不能采访,也没有第一手的“内幕”,如果不做过度解读还有什么办法吸引读者呢?想要更广的受众,这就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内卷”。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又没有素材的情况下,只能越来越拼。唐:我特别喜欢用俄罗斯套娃的结构去解读现在的秀,里面一层是产品本身,秀是上一层,大众的解读是外面那层。你可以说新闻稿是正史,但民间叙事也是很有帮助的,就像有一本《三国志》,还有一本《三国演义》。我们传统媒体就是“《三国演义》”,也是很认真地写的,的可读性。但民间解读可能就是“这些东西代表着品,是有钱人的东西,甚至是贪官才用的东西、来路不正的东西”。你不觉得很多在中国民间的叙事里已经变成坏品味的象征了吗?Sophie:Versace,东北人喜欢了。好吧,这是我的“刻板印象”了。唐:我觉得我们的审美是有问题的。大量的舆论宣传在文化断层之后,美其实也没了。我爸妈那时候没什么机会上学,他们给我的言传身教也是有限的。后来可以上网了,可以用VPN了,但大家发现趣味的意愿已经没有了。现在大家都在追星,整容过度成为了普遍现象。这种情况下,时尚也遭遇着一种尴尬处境,面临着过度解读或者误读,可能沦为坏品味的一部分,但同时也与这些“不正之风”联系在一起。比如你为什么不选择川久保玲?不穿Margiela呢?为什么永远都选那几个每个人都选的品牌呢?这样的选择就代表着这种选择有很大的问题。这种集体的选择就造成了民间叙述是负面的。因为美学也是需要进化的。可能小时候的你就是喜欢中规中矩。慢慢地,你可能觉得牛仔裤上剪几个破洞挺美的,再后来可能就开始欣赏解构设计了。时尚理念不断地在往前走,你也要跟上。比如我要穿了川久保玲的设计,我爸肯定会觉得我疯了。因为我爸的理念可能是保守的,而我则是先锋的。如果你不训练自己的眼睛,没有增加自己的经验,不多看不一样的东西怎么去欣赏不同的风景呢?否则的话你可能就永远选择LV、Dior和Gucci了,没关系你买呗。但对于品牌来说,产品在中国就可能会堕入一种糟糕的审美,一种负面的叙述中。可能是某个煤老板买了一条带者巨大“H" Logo的腰带。郭德纲也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但很他不懂时装。时装是一种语言,装饰主义、解构主义、洛可可,它有自己的词汇。如果你不理解这种词汇,只是凭借Logo去选择,不懂得如何用身体和时装的词汇去对话的话,后穿出来很可能是一场灾难,会把设计师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拽入一种糟糕的叙事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种奇异现象。Sophie:所以你认为杂志自己的公众号和纯粹的新媒体账号是在帮助品牌教育消费者?唐:肯定不能说都做得很好,有些就是自己拍拍照,美美地Po完图,完事儿,拜拜。Sophie:有些是用来教育的,有些是用来触及更多人群的。不同媒体的投放层级不一样,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唐:虽然很多KOL是为了挣钱,但他们的演绎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们的审美肯定好过普通人,他们用自己的品位去穿,是在帮助品牌完成一种新的叙事。但是说到教育就很难了。我承认肯定是能教育到一部分人的,比如我可能是吴岭的粉丝,我看她穿得好看,我也学她这么穿,我可能会穿得比她还好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竞争。(笑) 戚:小唐刚才说的套娃结构,如果我们还是用时装秀报道来说,这些年,媒体层面的解读和消费者层面的解读是不是很的断层了?唐:我修正一下,解读可能分三种,一种是体制媒体的解读,一种是自媒体的解读,另一种才是普通民众的解读。这三个里面,我个人觉得自媒体的解读更有趣,当然他们肯定会收品牌的钱,但他们作为个体、作为自媒体比体制媒体、机构媒体的舞姿更轻盈一些,他们的自由度更大,表现力也比我们相对要更真切。比如我挺喜欢吴岭的,她的表现就真实,所以你说的教育在某些程度上也是存在的。戚:当我们用媒体视角描述这件东西的时候,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阐述也好,介绍也好,教育也好,当一件东西成为一件商品进入商店的时候,大多数消费者还是且只是在乎它是什么牌子,以及它是否好看。而消费者对好看的理解其实还是浅显的,比如这个印花好看,这个颜色很正,这是否可以理解成普通消费者似乎就不在意品牌在讲什么故事?Sophie:我认为他们还是在乎的。那天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有趣的帖子,一个人说你怎么还买X牌这么low的牌子,我都买Y牌。底下一堆人评论,好奇怪啊,难道X牌不是比Y牌“高级”很多吗?消费者可能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是长期受媒体和自媒体的影响,消费者心中还是有一个评价体系在的,只是比较模糊,是一种感觉。唐:消费者收到的信息、所谓的“教育”可能是碎片式的、道听途说的。
Sophie:在品牌的强大且持续的营销下,消费者自身也是有感觉的。唐:这是另外一种宣传(Propaganda),比如说,“Impossible is nothing”,就是一种很典型的宣传语,只不过是很隐晦巧妙的。刚刚讲到大众的理解,其实里面还有一部分人是VIP,如果你买的足够多,就会被邀请去看秀,去VIP预览。但即便是经过了这样的“教育”,你也会发现不是每个人都乐意去了解背后的文化。 戚:这是大概率的事情吧?不过,有钱是可以任性的,我们没有在仇富。(笑)唐:我记得Chanel在成都办秀的那年,我在酒店吃早餐,看到有些就是VIP客户的女客人全身上下都是Chanel,踩着高跟鞋,手里拿着2.55走进餐厅。我在想,她们吃早餐为什么不能穿得舒服一点呢?我相信他们有很多Chanel,可为什么不选一个对的东西出现在对的场合?在上海,你会发现整体的美学肯定是会比其他城市要好的。比如我们集团的小年轻们有很强的视觉经验,甚至写稿也比我们好,这些小孩接受的教育、从互联网上得到的视觉信息肯定是我们的。我觉得历史一定会自我修复。中国有14亿人,有各种各样的城市,我说的只是我在上海看到的,我觉得我们比十多年前已经不止进步一个层次了,但如果到别的城市可能就没有那么理想了。我觉得真正的疗愈可能是“我买得起Chanel,但我为什么要买它”,到这种程度可能会好一点吧。Sophie:你刚说的品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太大、分层太多、文化又断层,要怎样才能让品牌在它应该传达的地方正确传达,这其实相当困难。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受众,一方面又不能失去自身的调性。就像明星在时装秀前发布微博说几点见,底下的粉丝就在猜测几点会有谁出现在秀里。看秀的人完全就是想看明星,但明星又不会出现在现场,这是奇怪的现象。唐:因为明星带货,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想看看明星穿了啥,背了啥包,自己也去买一个。这和时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Sophie:这是另一种时装,都在一个空间,但是你看不见,因为维度不同。唐:曾经时装是无所不在的,比如我在身上贴三个创可贴也可以是时装,只要方式是对的就行。 戚:所以时装解读在媒体层面和消费者层面是存在断层的吧。Sophie:消费者也分为时装精类、买包的,还有追星的。(笑) 戚:如果我们就是将这个范畴定位大众消费者,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他们更多还是在乎产品本身?唐:后还是要正面一些。比如一个小姑娘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但她买了一个单品和自己既有的东西做了很好的搭配,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说明美学和理解在往前走。品牌会给我们total look要求拍摄,我们也没办法,但这样就没有造型的必要了。如果是民间就无所谓了,把两个竞品放一起都可以,只要搭出果就可以。Sophie:时装还是一门生意。





